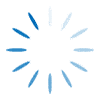人之将死其言也善,华郡主觉得这一刻她有太多的话想对爱子说,但时辰不多了,纵有千言万语也只能捡着肺腑之言说。
“修儿,娘有几句话,你勿要多言,娘只想你好好听着。”华郡主怕元修打断她,先声阻止了他。她看着城墙下的男儿,那是她的儿子,十五岁离家从军,二十五岁披甲还朝,从少年到青年,他一生里最好的年华,她一日未曾相伴。
但,从未后悔过。
“娘知道,参议朝政并非你的抱负所在,你一生之志在边关,可生在元家,这就是你的宿命。人终有逃不脱的宿命,娘任你戍边十年,不是望你成就何等的功名,而是想让你过一段想过的日子,从少年到青年,一生里最好的年华不被宿命所缚。日后你若归京,大漠关山,你见过,烈烈长风,你吹过,巍巍关城,你守过,这一生终是不负!”
这十年,每个夜晚,她的心都在西北。每一回他出关,每一回他领兵,她都日夜难安,终日守着西窗,直到京中传来边关捷报。自他离家,她屋里少了个日日请安的人,院子里少了个天天练拳的人,府里少了道明朗的笑声,这些一缺就是十年。他归家那日,长高了,晒黑了,眸底的笑却如烈日般刺眼,衬着那身战袍,那一刻,她觉得身为娘亲,十年里缺的那些都是值得的。
“娘知道,你一生都想留在西北,不理会朝廷纷争,只守着边关,自由自在。可是儿啊,天下间哪有那样的自由自在?如若当年不争,如今这世间恐怕就没有元家,没有你了!即便现在不想争了,你姑母贵为太皇太后,你爹贵为丞相,你守着西北国门,麾下有三十万重兵,关外便是大辽!哪个帝王能容得下你?”
“圣上若亲政,头一个要杀的就是你姑母和你爹!即便他顾念你十年戍边之功,只论功过,不论私仇,准你戍守边关,你能保证圣意一生不改?即便当今圣上真乃千古开明之君,你能保证日后的储君也如此?你能保证大兴的帝王都如此?削兵权是迟早之事,轮不到你也会轮到你的儿孙!”
“娘今日的话你记住——普天之下,皆是王土,四海之内,皆是王臣!江山一日非你所主,自在一日不由你说了算!”
华郡主长叹一声,原以为就算缺了十年,日后他们母子相处的时日还长,有些话总有时间说,可是没想到忽然之间就走到了今日这一步。
春阳当头,华郡主深深望了眼马背上的男儿,缓缓闭上眼。眼前是那日儿郎披甲归家的爽朗笑容,那笑容比今日的日头暖多了……
儿啊,其实娘希望你一生都能像那日那般笑着,其实娘……希望你没投生在娘的胎里,没投生在元家,这样便可开怀一生,不必夹在家国之间,难以两全。
可是你就是生在了元家,这就是你的命,你的抱负与性命,若要娘选,娘希望你活着。
愿娘的苦心,你懂!
华郡主忽然睁眼,城墙下起了风,那风吹起女子散乱的宝髻,步摇轻扬,击出金脆之声,玉牙咬上舌根,口中漫开血气!
“元谦!”
城下忽然传来一声怒喝,长风卷着血气冲上城楼,内力震得华郡主的心神一醒!她睁开眼,见城楼下,元修怒望而来,手握马鞭指向元谦!
这是他头一回不称他为大哥。
一年前望关坡之叛,今日城门楼之迫,终在数次咄咄相逼之后,将男子逼出了真怒。
“你不只要报仇,你更要盛京,要江北,要天下!那就放人,我当你的人质!”元修望着城楼,痛苦哀悲皆已不见,马鞭若弓弦,直指元谦!
“修儿!”华郡主欲阻止。
元修听而不闻,“我受了内伤,敢上城楼,你可敢换?”
元谦扬了扬眉。
元修继续道:“天下才是你今日所图,报仇,逼迫,不过是余兴之乐。你在等圣驾和百官回城,以谋大利,那就别怪我没提醒你,我受了内伤,现在还能上城楼,圣驾到了可就上不了了。”
他若为质,圣上不会看着他死,否则必失西北军心,而爹也不会看着他死,所以待圣驾及百官回城后再谈换人质的事,阻力就多了,不如现在谈。
元谦却笑了笑,“你果然都明白。”
他都明白,却还是肯自废功力,甚至不惜性命,正因如此,他才不喜欢这异母所出的弟弟。他自幼费尽心机谋活路,为练这身武艺险失性命,而这些他轻易就有,却如此轻付!
“换,还是不换!”元修的神情犹如一潭死水。
“换。”元谦答时举目远眺,望着长街尽头虚了虚眼,“不过,你为何会以为你一个人可以换两人?”
元修眉峰一压,但闻长街尽头正传来阵阵马蹄声。
“你只可换一条人命,若想换两条,需她一起上城楼!”元谦迎风远眺,淡淡笑道。
长街尽头,人来得颇快,方才还在远处,说话时已瞧见了人影。
元修和西北五千精骑一同回首,但见来人伏在马背上,人与雪白的战马融在一起,神驹驰如电掣,人马犹如白电,不见那人容颜,唯见发如浓墨,乘风泼来,到了近前勒马急停,势如住剑!
马停蹄,人仰头,春日照见那张容颜,见者屏息。
元钰被绑押在城楼上,望见神驹的一刻似有所感,一年未见,即便只是远远望见,她也知道是那人。只是没想到待人近时,勒马仰头,望见的却是一张陌生的容颜。
那是一张少女的容颜,十七八岁,身居马背,身披战袍。长风吹不过筑了六百年的古城楼,少女的目光却似晨辉,清冷,迫人,仿佛南国的雪,北原的竹,难得一见的风姿,于这巍巍皇城之下生出一道挺拔风姿,让人望见一眼,那身影便似在心里扎了根。
陌生的容颜,熟悉的战甲,城楼上被绑着的少女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,震惊地瞪圆了眼。
华郡主早知暮青可能是女子,但当真的看见,仍免不了震惊。
元谦笑了声,“果真没猜错。”
暮青冷冷地望着他,却没打招呼,而是将目光一转,见元修面色苍白襟前染血,皱了皱眉头。
“药呢?”暮青问孟三。
孟三在元修的战马旁站着,听闻此言一怔,赶忙从身上摸出只药瓶来,此药对救护心脉有奇效,只是不知对内伤有用无用,因此他就没拿出来。
暮青见元修果真没服药,面色更寒,“有药不吃,你是想说,我当初剖心取刀的力气都白费了?”
当初冒险取刀就是为了把他从鬼门关前拉回来,可如今他有药却不肯吃,既然找死,当初又何必费那工夫?
元修一声不吭,把手往孟三面前一摊,孟三愣了愣,倒出几粒药来,眼睁睁看着元修仰头将药一口吞了。
孟三眼神发直,大将军肯服药了?
在边关这一年,不发心疾,大将军可是从不服药的,每日到了服药的时辰,他就觉得自己要挨军棍,因为每日把药端进书房,再进去时,那药必定还放在原处,动都没动。顾老将军苦劝无果便拿军法命令他,说若是大将军不服药,他就去领军棍!那日他哭丧着脸到书房里送药,把老将军的军令说给大将军听,还以为他能就范,结果便听大将军说:“那就去领吧,在营房里多趴几日,省得天天来送药。”
他把这话回禀给老将军,老将军气得把他撵了出去,隔天还是一样的话,劝不进大将军服药就等着挨军法!他每日都从书房里哭丧着脸出来,再从老将军府里滚出来,日子简直别提多苦,简直不是人过的。
今儿跟谦公子在城门前对峙,他还以为大将军会倔得跟头驴似的,死撑着也不肯服药,可咋都督只冷言冷语了一句,他就一声不吭地服下去了?
这简直是欺负人吧?
孟三瞄了暮青一眼,瞄见她那张今日才见到真容的脸上时,古怪地把目光转开。
这时已经不能叫都督,该叫皇后娘娘了吧……
华郡主看着暮青,见少女冷眼望着城墙,再看看元修,见他也执缰望着城墙,两人谁也不看谁,一样的英姿凛凛。但在她这当娘的眼里,却看得出她的儿子虽没看身旁的少女,那眉宇间却全是别扭的在意。
她忽然便想起前年修儿回京,她一有机会就劝他见见宁昭,他却说已有意中人,是朝廷三品官府里的小姐。
她又想起修儿自戕那时,曾于病榻前唤一女子的闺名,那闺名里有个青字。
原来是她……
原来真是她!
这世间竟有从军入朝的女子!
华郡主的眼中忽生利芒,这女子与圣上之间不清不楚的,实乃祸水!
正想着,元谦的声音从旁边传来,“好了,既然不想叙旧,那就不必浪费时间了。”
元谦看向元修,抬手丢了把刀下来,玩味地道:“你若想救这两人,需拿你和她换,拾起刀来,押她上来。”
默认冷灰
24号文字
方正启体
- 加入书架 |
- 求书报错 |
- 作品目录 |
- 返回封面